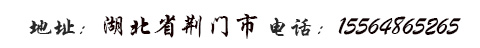缓刑已满的少年犯,怎么也走不出惩戒期
|
治疗白癜风用甲氧沙林液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dfyc/170224/5231253.html 缓刑已满的少年犯,怎么也走不出惩戒期 转载自人间thLivings 老实巴交的袁谷立因为有前科,没租成门面房,这次是当年的同案犯郑强来租了,你嫂子怎么不反对了?王科长被我说得满脸通红,憋了半天,冒出一句:“郑强这号人,咱都犯不上为了公家的事情跟他‘结仇’不是?” 作者:深蓝 前言 年6月的一天,晚上10点左右,17岁的高中生袁谷立与同学郑强、杨晓云3人因上网费用耗尽,被网吧老板赶到了大街上。 他们决定去附近的小区“搞点钱”,钻进楼道,原本打算偷辆电瓶车卖掉,却发现谁也不会开电动车锁。3人正沮丧时,1名刚下晚班的中年女工走进楼道,少年们临时起意,决定打劫这名女工。 袁谷立手持一字改锥,郑强拿着挂在钥匙上的折叠水果刀,杨晓云则从楼道里随手捡起了一根木棍,他们将女工逼到墙角,用从电影里学到的“狠话”抢走了女工的手提包——里面仅有21.6元现金和一部价值元的手机。 3人失望透顶,拿着打劫来的现金去了小区隔壁的宵夜摊,一人点了一份炒粉,边吃边商量着去哪儿把手机卖了。女工一回家就报了警,警察循迹而至,仅用半个小时,便将他们按倒在了宵夜摊上。 当家长们赶到派出所时,3个少年正痛哭着坐在讯问室里等着做嫌疑人笔录。袁谷立的父亲、年过半百的采油工人老袁,走上前来,扬手便狠狠给了儿子一记耳光。 家长们都恳求警察看在涉案金额只有21.6元的份上给孩子们“一次机会”,他们回去一定好生教育。但依据《刑法》规定,涉案金额并不是抢劫案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,3人涉嫌“持械抢劫”,依律应当从重处罚。 最终,在家长们的不断致歉和主动赔偿下,受害女工谅解了3个少年。加上案发时3人年龄皆未满18周岁,还是在校学生,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了从轻处罚:袁谷立、郑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,缓刑3年;杨晓云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,缓刑2年。 1 年7月,袁谷立和郑强缓刑期满,因期间没有再次犯罪,法院最终决定撤销执行为期1年的实刑。按照规定,两人会前来派出所报到,由我给他们建立《重点人口管理档案》——1年前,同案的杨晓云已在建档后远赴深圳打工了。 我先见到了袁谷立。第一次见面,我甚至不太相信,这个和我差不多高、戴着眼镜的腼腆少年,会是个刚刚刑满的抢劫犯。 19岁的袁谷立端端正正地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,一板一眼地回答着我的问题。我让他把当年的案情复述一遍,他花了将近1个小时,才事无巨细地讲完。 我又按程序问了他一些诸如“是否认识到自己的罪行”、“是否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”之类的问题。最后,问到他今后的打算时,袁谷立说自己还想上学。 袁谷立犯案就读于市三中,3年前甫一落案,就被学校开除了学籍。他说,本来自己学习成绩还可以,这几年也没有放下功课,自己一直坚持在家学习。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,但还想上学,总归是件好事,于是便鼓励他不要自暴自弃,之后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交流。 就在袁谷立下楼拍登记照的间隙,老袁低声问我,他儿子这种情况,还有没有可能回去继续完成学业?老袁又补充说,袁谷立是家族里这一辈中唯一的一个男孩,从小就被寄予厚望,虽然之前走了弯路,但毕竟年纪尚小,还想谋个前程。 此前我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,只能建议老袁先去三中咨询一下,老袁说他早就去问过了,学校说当年的事情太过恶劣,现在也不同意接收。 “那其他学校呢?”我问老袁。 老袁叹了口气,说能问的都问过了,没有学校愿收。他求我去学校帮袁谷立“说句好话”,也许学校会看在派出所的情面上,对袁谷立网开一面。 我不知道这事儿是否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,但看父子俩如此诚恳,也为了之后方便“重点人口”的管理,便答应了下来。 我解释说自己去也只能帮忙咨询,最终结果确实没法保证。即便如此,老袁还是一再向我道谢。 袁谷立登记完好一段日子了,同案的郑强也没来派出所。 郑强有个姑姑在本地,是他唯一的亲戚。我找到她询问郑强的去向,她就像躲瘟神一样,一听到侄子的名字便直晃脑袋,说自己不知道。 一天在辖区网吧做例行检查时,我偶然发现了郑强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派出所登记,郑强说忘了。我把他拉回派出所教育了一番,问他今后打算干什么,他说“无事可做”。 “和你同案的袁谷立打算上学,你有没有类似想法?”本着上级对未成年案犯要求的“管理与教育并举”的原则,我还是多问了一句。 郑强脸上写满了轻蔑:“上个屁学,犯事之前就不想上了,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,还去找那麻烦干啥?学出来有个鸟用?” 我叹了口气,说不想上学也没事,只要好生待着,别干违法乱纪的事情,按时回来找我就行。郑强一边应付地点点头,一边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要点烟,我瞪了他一眼,把香烟从他嘴里夺了下来。 2 我一心惦记着袁谷立读书的事,半个月之后便去了趟三中。校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,却对袁谷立回校读书一事坚决不允。 校领导跟我讲了学校的难处——毕竟“持械抢劫”影响恶劣,案发当年,学校的宿舍管理员、班主任、级部主任和分管校领导都受到了相应处分,他们3人的班主任,直接被调离了教育系统。 现在让袁谷立回来读书,学校既无法向在校学生和家长交代——没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和“刑满释放人员”做同学;也无法向当年被他们牵连的老师们交代——老师们档案里的处分尚在,涉事学生却回校读书了,实在说不过去;再者说,袁谷立当年被开除了学籍,现在入学也不符合高中生学籍管理的相关程序。 校领导看上去也非常为难,建议我:“要不让他去私立学校问一下?” 等到11月的季度谈话,我没有像惯常那样把袁谷立叫到派出所,而是专门去了他家一趟。一来想看看袁谷立在家的真实状况,二来也反馈一下帮他联系学校的结果。 我到的时候,袁谷立正在餐桌上做题,见我来了,赶忙站起来打招呼。我拿起习题集,是一本文科数学的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,顺手翻了翻,大概做了一半左右。袁谷立说自己一直在家里复习,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。 我鼓励他继续加油,随后又私下里给老袁转告了之前去三中咨询的情况,建议他去找找那些私立高中,看能不能把儿子塞进去,哪怕多花些钱。 老袁一直抽着烟,听我说完,长叹了一口气,说他已经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。他已经在重庆找到了一所私立学校,但因离家太远,还在犹豫。 我说,袁谷立是本地户口,能在重庆参加高考吗?老袁说,学校说按规定是不行,但只要老袁愿意出10万块的“建校费”,他们有路子,可以帮忙操作。 我劝老袁,这事儿得再想想,现在“高考移民”查得严,没听说过花10万就能搞定的。省内也有不少私立学校和“复读学校”,没必要去那么远。 老袁说行不行的还是试一下吧,帮忙办事的是自己一个朋友,“办不成的话钱能退”。 半个月后,老袁给我打电话,说儿子去重庆了,问我之后的“季度谈话”怎么办。我告诉他可以改成电话访谈。聊了一会儿,老袁一直支支吾吾地不肯挂电话,好半天才怯怯地问我,以后给袁谷立打电话时能不能提前先发个短信。他说自己之所以舍近求远把儿子送去重庆,主要也是考虑那里没有人知道袁谷立犯过事。 我答应了。 之后的几次“重点人口谈话”,袁谷立的精神状态一直都不错。他说自己与同学和老师相处得都挺好,虽然落下了很多功课,但一直在努力跟进。他还说,自己已经有了心仪的大学,以后还要考研究生。 “一定全力以赴!”袁谷立在电话里坚定地对我说。 相比袁谷立,郑强则一直“行踪诡秘”,极少按时来派出所找我。给他打电话,他总说自己忙,我问他忙啥,他就含含糊糊的。 偶然一次机会,我又在辖区的一家饭店遇见了郑强。他不知什么时候把自己身上纹得花里胡哨的,正在和一帮“社会人”在包厢里吆五喝六。席上还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,全是辖区里的不安分分子。 我把郑强叫出来,问他为什么一直躲着我。他推脱说自己是在忙“工作”。我指了指屋里,问那就是你的“工作”?郑强打着哈哈说,都是朋友,凑在一起吃饭聊天而已。 我看郑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,心里来气,于是搭着他的肩膀回了屋里,说:“上季度重点人口谈话你还没做,你平时那么忙,咱俩见一面不容易,要不今天就在这儿把季度谈话做了吧。” 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。很快,一个40多岁、貌似“大哥”的男人站起来,瞪着我,一脸凶相,旁边马上有人拉住他,还有人立刻摆出一副热情的面孔:“李警官,今天怎么有空儿……”一听此言,“大哥”一抹脸上的不快,还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。 我把烟接过来,放在桌上,打开录音,跟众人说:“你们先聊着,我和郑强谈个话。”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,谁也不说话,反倒是那个“大哥”一脸假笑地接了茬:“李警官,按说这个重点人口谈话,不能在公共场所做吧,重点人口也是有隐私权的……” 我笑了笑,说:“你还知道这个,看来也是同道中人?姓甚名谁告诉我。”说完,我便把警官证扔在桌子上。 “大哥”愣了一下,很不情愿地把信息告诉了我,我在警务通查了一下,果然,也是公安网上挂了号的。我问他跑到我辖区来干什么,他就讪笑着说,“朋友聚会而已”。 我看了看桌上另外几个人,又拍拍郑强:“下次我再找不到他的时候,还烦劳各位给我传个话,不然我得亲自去找你们要人。”一众人都连连点头。 谈话当然不会在这里进行,警告的目的达到了,我便起身离开。郑强出门“送”我,我点了点他,说年纪轻轻,别总给自己“挖坑”。 郑强就抱怨起来,说,不就是上次谈话没去派出所嘛,“又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,至于这么整我吗?” 我说你知道就好,下次季度谈话再找不到人,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。 郑强听罢,没再说话。 3 年7月,我和袁谷立谈话时问起他的高考成绩。袁谷立非常不好意思,说自己最终还是没能在重庆本地参加高考,临考试前回了本市,可两地的高考试卷不太一样,最终只考了多分,没能上得了大学。 我扭头问老袁,问之前花的钱呢?老袁一脸怒气,说自己被那个“朋友”骗了。 我说这明显属于诈骗性质,有没有报警?老袁摇摇头,直说“算了算了”。我再问,老袁却不知有什么顾虑,不再接茬儿。 我叹了口气,问袁谷立之后有什么打算,袁谷立没说话,老袁却接话说:“不考大学了,让他学点技术,之后能找个工作养活自己。”他说已给儿子在本地一家有名的厨师培训机构报了名,过段时间就去上学。 我问为何不让袁谷立再考一年,老袁的神情便满是沮丧,说,就算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,“他可是戴罪之身,以后还有可能翻身吗?”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,老袁就失望地看了儿子一眼,说等会儿跟我说。 等我把袁谷立打发出去后,老袁点了支烟,狠狠吸了一口,才说,这些年其实他一直在四处打听,想问问看之前那个缓刑判决会给儿子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。本来他曾乐观地认为,只要儿子在缓刑期内好好表现,不被收监执行实刑,以后也不再惹事,时间一长人们便会忘了。 但,现实却让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绝望。这起刑事案件几乎让儿子“前途尽墨”——无论是升学、当兵、就业、考公、提干,都有一个“无违法犯罪记录”的门槛拦在前面,“就算考上大学,他以后也考不了编制、当不了兵、进不了国企,稍微好点的工作单位都不会要他,还不是得四处打工?与其那样,还不如学个手艺算了”。 我嘴上虽然劝着老袁,但自知这也没什么别的办法。 老袁转而又问我,之前和袁谷立同案的另外两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,我说杨晓云一直在深圳打工,还算老实。但郑强那家伙不太省心,去了一家“小额贷款公司”,说是当“业务员”,但应该就是在“收账”,身边交往的也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人,我最近打算再“敲打敲打”他。 老袁马上接话,说这个郑强真不是什么好东西,当年,袁谷立其实根本就不缺钱,就是因为郑强的拉拢和威胁,袁谷立才勉强答应去帮郑强和杨晓云“站场”,结果却落到了现在这步田地,算是被郑强害了。 我没有接老袁的话,之前的案子判都判了,该说的也都跟法官说过了,现在再提没太大意义。我也只能跟老袁说,以后注意,让袁谷立别跟郑强走得太近,断了联系最好。 老袁使劲点头,说儿子早和郑强他们“划清界线”了。 那段时间,我一天到晚都得紧紧盯着郑强。 上次在饭店的“警告”似乎对郑强的效果十分有限。他还在收账,常带着两个“小弟”开着辆斯柯达在辖区里转悠。我问他车子哪来的,他就说“公司”给他配的。 我按照车牌联系到车主,车主在电话里说,车是被郑强一伙“顶掉”的——他之前打牌输了钱,临时从郑强所在的贷款公司借了块,这十几万的车子便被郑强等人开走“抵押”了,到现在不还他。 车主又跟我抱怨了一通他被“黑社会”威胁的经历,我让他来派出所报案,他口头答应了,但最终也没有来。 那段时间,常有人反映郑强等人上门“收账”时泼油漆、砸玻璃,还威胁要“卸人胳膊”,我不胜其烦,找郑强出来问他想干什么,他就对那些事情矢口否认。我暂时没有证据,只能警告他“记着自己现在的身份”。 郑强嘴上答应着,转头,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 那时的郑强俨然已成了混子圈里的“后起之秀”,他不但毫不忌讳自己过去的经历,反而将其当成自己的“光荣历史”,据说道上的混子们还挺“尊重”他,年纪轻轻的,就已有年龄大他一轮的混子喊他“强哥”了。 有次,一位夜市摊主悄悄告诉我,郑强常带着一伙“兄弟”在他的摊上吃霸王餐,一群人招摇吵闹,故意光着膀子露出文身,吓得其他客人都不敢光顾。我让他下次遇到就打电话报警,“寻衅滋事办的就是他们这号人”。 摊主点头说好,但之后从没打过电话。隔了段时间我问他,是不是郑强一伙不去了,摊主却摆摆手说:算了,在街面上做生意不容易,见谁都得点头哈腰,听说郑强以前坐过牢,心狠手辣,自己不想得罪他。 郑强的“名声”越来越大,领导让我加强对他的管控力度,可我也不太可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去盯郑强一伙,思来想去,只剩郑强的姑姑了。 我找到她,说希望她能够帮忙管教一下这个侄子。但郑强姑姑却说自己和郑强没有关系,“以前上学时还回来睡个觉,把我家权当宾馆。现在混社会了,再不回来了”。 我也去找过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,他们也说郑强“生性顽劣”,从小就是有名的坏孩子。居委会的治安干事和郑强姑姑住一个大院,跟我列举了一堆郑强从七八岁开始犯下的“劣迹”,什么往厕所里扔鞭炮,偷邻居的自行车……但当我问能不能帮忙看管时,那位40多岁的女干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:“管不了管不了,他这号人谁敢管?” 说完,女干事大概也觉得刚刚自己表现得有些不合适,找补说,她可以帮忙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wannianqinga.com/jwfss/1090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绿氢如何摆脱羁绊,迎来发展春天
- 下一篇文章: 网吧与网上冲浪的那些年